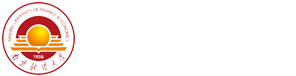简介:
《信息文萃》是一本图书馆内部发行刊物,于2000年创刊,每年出版16期,由财经、高教和读书思考三个栏目组成,每期共8个版面,包括教育类4版,财经类3版,读书思考1版。至今已出版261期。《信息文萃》精心选摘与主题相关的时事要闻、经典评论,将初步筛选的信息编辑整理,《信息文萃》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势热点,求真务实,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苏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由意识
摘录: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更新日期:2019年05月13日 14:41 类别:图情天地 总浏览:3749

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 月)是这套五大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第三卷。作者在“前言”中说本卷的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的那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虽然他也曾经和其他评论家们一样希望迅速越过这一时期,以便尽快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的那几部重要小说,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越过的时期。我在读完全书之后更加觉得,这个时期不但对于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来的创作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回顾我们时代自身的思想与文学发展历程也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两年多前我在关于本书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的书评中曾经谈过,该书第四章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入狱后受审的情况,但是弗兰克没有简单地依据材料罗列事实,而是力图从中发现和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思想,并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从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警察局的“自供状”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意义和思考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在第三卷发展得更为成熟,所揭示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更为复杂和更为波澜壮阔与激动人心。如果说第二卷的“受难”拉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政治斗争生涯的序幕,第三卷的“自由的苏醒”则是让他走到了俄国思想政治舞台的中心,让他的思想发展与表达中的所有曲折、微妙和重大的变化呈现出来,揭示出在这几年中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如何产生决定性的改变,从而成为理解他后期的重大创作成果的坚实桥梁。
在经历了十年的监禁和服役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0年回到彼得堡,这时“他只是在那个令人振奋的自由化和改革时期如潮水般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众多流放者之一”。虽然没有到车站恭候,秘密警察还是马上就盯上了他,继续监视他的活动,似乎没有这种待遇就无法证实一个人在时代思想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为重返生活和重新建立文学声誉而奋斗,这时他内心的坚强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他获得成功的唯一保证。在牢狱中他为所接触到的下层人的残酷和自私感到震惊,同时也发现即便是这样也能在他们身上发现仍然残存的传统基督教信仰,使他相信在俄罗斯农民的精神核心中仍然保有仁爱和牺牲的基督教美德,这对他日后的思想感情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说他从最近十年惨痛的经历中获得了什么新的信念,如果说命运之手对他的打击让他得到了什么教训,那就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两个无法规避的事实。一个是人类的灵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维护其自由的愿望;另一个是,基督教博爱和自我牺牲的道德观念是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最高需求。农民囚犯天生的基督徒品性使他在苦役营的黑暗中看到了唯——线光明。如果没有这些道德价值观念的传承,生活在他们当中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简直就是生活在地狱里;因此,他一想到激进派现在打算破坏和毁灭的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就不寒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急欲重返的文坛激荡着思想斗争的漩涡。在文学基金会组织的第一场慈善活动中,屠格涅夫朗诵他新撰写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并引起激烈争议。俄国文学中的“哈姆雷特”就是那些“多余人”——心地善良但软弱无能而且完全不切实际的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子;“堂吉诃德”在俄国就是指年青一代中有坚定信仰和准备为民众的事业牺牲自己的那些人。虽然屠格涅夫对后者表示赞扬,但是年青的激进分子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虽然没有公开抨击屠格涅夫的这篇文章,杜勃罗留波夫利用屠格涅夫发表下一部小说《前夜》的机会表达了他们的不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立场基本一致,但是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无论如何,从他重返文坛之日始,思想上的争议和站队就成了他无法回避的局面。在四十年代的“旧人”与六十年代的“新人”之间、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贵族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之间、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和乡土主义之间,思想斗争的浪涌一波波席卷而来,在这些思想漩涡中前行需要有信念、立场、观点、策略、勇气等引领。该书第四章“一种新的倾向:乡土主义”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作为乡土主义者挺身参加了六十年代的报刊大论战,他的活动也因此受到密切关注;历史学家也认为,乡土派作家相当优雅地阻击了俄国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这场论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时期是全面参与了俄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大论战。“他不仅与左翼激进派(《现代人》杂志)、左翼自由派(《祖国纪事》)和自由中间派(《俄国导报》)论战,而且还对新出版的斯拉夫派的《日报》发表看法,后者代表了独立的保守派观点,与政府的官方出版物不同。人们可以暂时认为他与斯拉夫派的关系是他对激进派的态度的反面:尽管个人不赞成斯拉夫派的社会偏见,但他仍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他从四十年代俄国的西方派阵营中走出来,逐渐接受了斯拉夫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但是又完全不接受斯拉夫派那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不赞成他们对前彼得大帝时期的怀念和对俄国的新文学排斥。他与激进派意见分歧的重点是认为他们急于求成,指责他们想要实现只有在俄国社会发展的未来阶段才能实现的变革。他还担心,激进派的公开对抗活动将导致当局重新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使那两年俄国社会可以稍微呼吸一下自由空气的局面得而复失。
在苦难中苏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追问自由的含义和价值,而且充满了反思与警惕。前面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十年的苦难经历中获得的信念之一,就是人类的灵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维护其自由的愿望。在日后他笔下的苦役囚犯的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会令人难忘地看到那些囚犯们认为比任何东西都宝贵的是“自由或者自由的梦想”;为了坚守这种梦想,他们有时甚至会采取疯狂的行动。在看待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理想的问题上,他同样把自由作为核心价值予以考量。“如有必要,他宁愿受苦也不愿在一个自由将被当作原则问题予以消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里过富足的生活。离开苦役营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把他在那里度过的几年比作生活在一个‘强制性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说法表明,他下意识地把苦役营的情况与激进派梦想的某些乌托邦社会如果实际上实现的话可能导致的后果联系起来。此外,仿佛故意地一样,俄国激进思想的最新突变以明显的方式无可辩驳地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本能意识到的苦役营里令人无法忍受的个人自由的缺失与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科学’思想之间的关联。”“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是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它非常强烈以至不可能被压制,即使以无尽的财富将其淹没也不行。”而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自由这个问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大的障碍,所以他将其归为空想。他不让这个问题再次出现,……”
最后,我们还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今天,在文学经典阅读之外,如果我们忘记、轻视甚至是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将会怎么样?尼·潘琴科在为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写的“俄文版序”中曾经说,曼德施塔姆夫人指出苏俄“知识分子”的罪孽是在“胜利者的统一意识形态”前缴械投降,放弃道德标准和全人类价值,他认为这就是抛弃与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果。另外,在我看来,即便只是从公共声音与美学的关系角度来看,假如在一个时代中铺天盖地而来的声音充满了傲慢与自负,同时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里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嘲弄与轻佻,而听不到一丝审美嘲讽的声音,那么在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珍贵——他在《群魔》中对那些令人讨厌的人说:“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当然,看起来那些人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摘自《澎湃新闻》2019年4月11日)
最新文章 TOP10
热门文章 TOP10